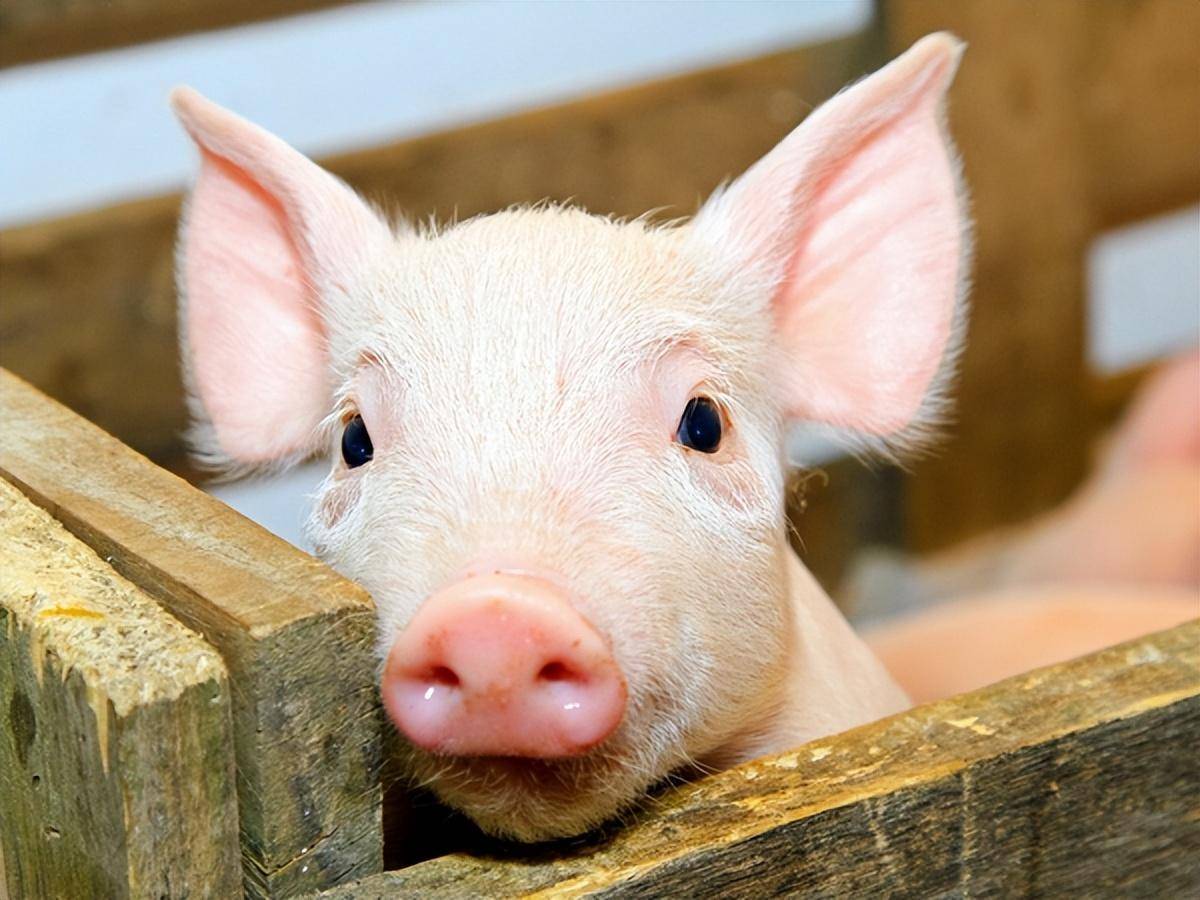
作者:朱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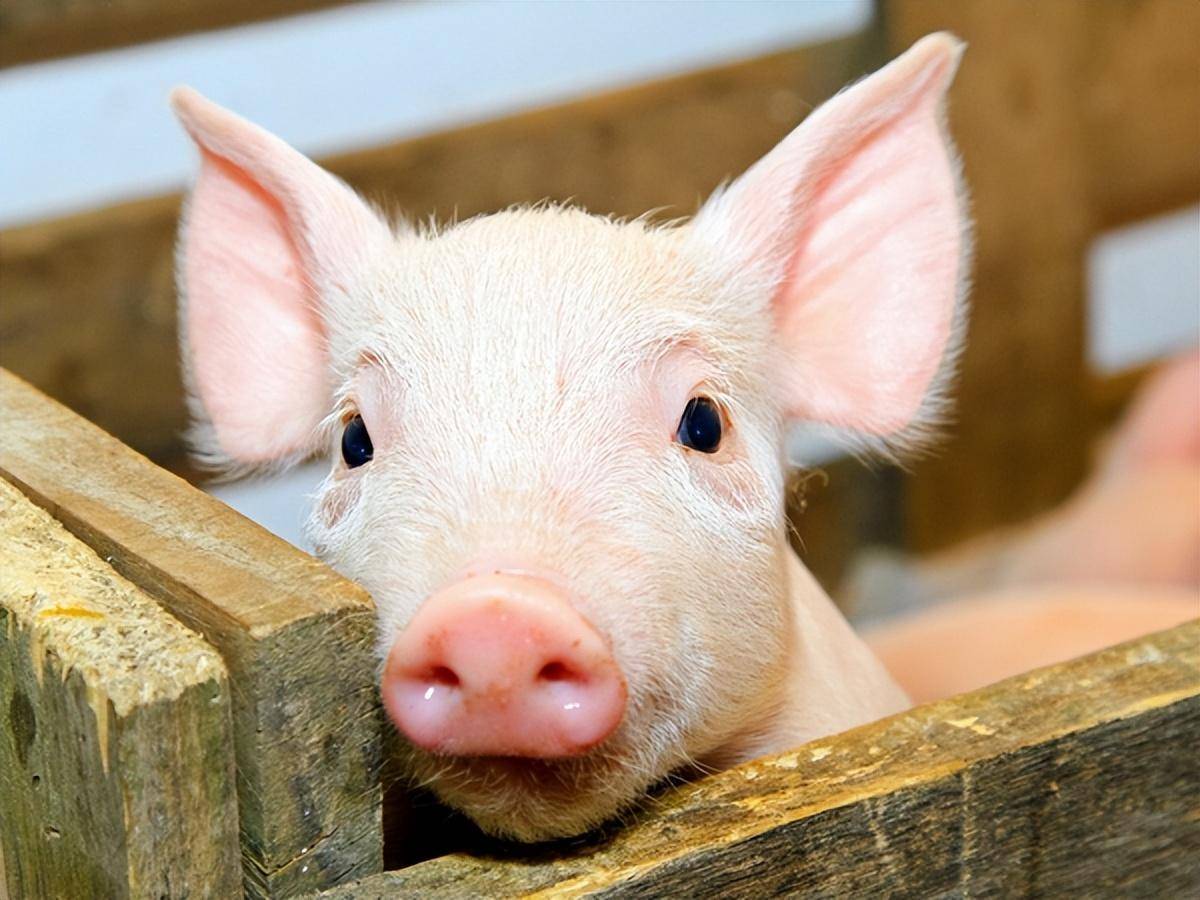
1968年秋天,我们到宝鸡县坪头公社下乡插队,那一年我十六周岁。
正是长身体的时期,山里的农活一出工就得爬坡上山,体力消耗大,我们都很能吃。但是,当年山村里缺菜少油,主食多为杂粮,自己做饭,又总是对付,所以一年四季,我们仿佛总没吃饱过。那段岁月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,就是那种饥肠辘辘、垂涎欲滴的感觉。
当年,这种感觉每一天都在困扰着我们,饱餐一顿,几乎成为我们无时不在期盼的盛大节日。怎样摆脱这种窘境呢?几个同学一合计,决定养猪养鸡。于是,一位家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同学自告奋勇到西安,在师大农场买了一头纯种约克夏小猪和十来只小鸡。这些鸡的命运很不好,还没等长大全被黄鼠狼叼走了,我们连一口鸡汤都没喝上。然而,我们养猪的经历,却很成功,成为当地的一大新闻,也成为我们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津津乐道的往事。
小猪带回生产队那天,村民们纷纷到知青点看稀罕。那时候,村民们几乎家家养猪,但他们养的都是土猪,身黑嘴短个小,长得很慢。这种白毛长嘴长腰身的约克夏猪,山里人还是头一次见到。他们一边看一边说:“知青真有本事,弄来了一头外国猪。”也有的村民调侃我们:“知青连自己都喂不饱,还能养猪?”
我们开始了养猪的经历。头些日子,我们的热情很高,一下工先看小猪,顾不上做饭,先给小猪开伙。小家伙跟我们也不见外,我们围成一圈吃饭,它跑进跑出要吃的,仿佛就是我们中间的一员。没多长时间这股热劲儿就过去了,我们劳动回来,累得腰酸腿痛,往炕上一躺,连自己的饭都懒得做,哪还顾得上猪?可这头小猪的食欲简直是太好了,整天琢磨着吃,我们一进门,它就哼哼唧唧围着我们转,嘴在我们身上拱来拱去。心情好,我们就给它弄些吃的;心情不好,就如它打山门处任它门上境境土地馆哪 所以,这头小猪跟着我们 有一 顿没一顿、饥一顿饱一顿地也过着“知青”生活。但小猪的生命力实在太强了,即使是这样的日子,它也像吹了气一样,很快长了起来。它好像很懂事,我们走到哪儿,它就跟到哪儿。于是,村里又添了一道风景:知青们到队里参加社员大会,身后跟着一头白猪在周围晃悠。村里人都说,知青把猪养得跟狗一样“灵性”。从那时起,我开始认为人们把猪与“蠢”联系在一起,绝对是一种偏见。
不知不觉中,小猪长大了,七八个月以后,已经是村里猪中间的“巨无霸”了。它的食欲越来越大,大得我们实在应付不了。每天我们一下工,它就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,用嘴拱开灶房门,一如既往地在我们腿上拱来拱去。猪小的时候,这样还挺好玩,现在这么个“巨无霸”,拱来拱去就不那么好玩了。一次,同学们正忙着做饭,锅里的水烧开了,一位同学一手拿着切面刀,一手揭锅盖,它上去一拱,差点儿把同学拱到开水锅里。同学一急,也没顾上手里拿的什么东西,就向猪身上砍去,这一刀砍在了屁股上,猪嗷地惨叫了一声向门外冲去,一连几天没敢回家。
有时,我们外出几天,猪就成了村里的“流浪汉”。它本事还挺大,闻见哪家猪圈有猪食味儿,总能撞开门拱进去。农民家的土猪遇见它,就像普通人遇到相扑运动员一样,毫无抵抗之力,只能躲到墙角委屈得哼哼。我们回来后,村民们向我们“告状”,我们则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,装糊涂,村民们也无可奈何。后来,村民们知道我们不在,也时常帮我们喂猪。说实话,我们养的这头猪是吃“百家饭”长大的。
习惯了流浪生活,这猪就不愿在窝里待着,长长的身子在村里晃来晃去,走到哪儿,歇到哪儿,吃到哪儿,很快就长得近两米长。这时,它更有名了,周围村庄的农民纷纷跑到我们村参观这头大得出奇的洋猪。他们望着它那伸展开来呼呼大睡的身姿啧啧称奇。事情也传到了公社,公社的养猪场专门派人来看,他们也没见过这么大的猪,便对生产队队长说:“谁也不准帮知青把这头猪杀掉,必须交给养猪场。”
送猪那天场面颇为壮观。从生产队到公社有很长一段路,要上坡下坡,渡渭河,穿隧道。我们几个男知青外加四名社员,前面哄,后面推,前面拉,后面撵,费了好大的劲儿,花了半天时间才把它送到公社。这头猪的驾临轰动了公社,一条街的人都拥来看这头罕见的大洋猪。一上秤,四百多斤,抵上农民养的三头土猪!养猪场场长为了感谢我们,把这头猪评为“特级”,给了我们近二百元钱的报酬。对我们来说,这已是一笔“巨款”了。但是,在回村的路上,我们几个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毕竟养了近两年时间啊!
这段经历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,但我还是时常泛起对那段往事的回忆。想起那段蹉跎岁月,想起大山怀抱着的小村庄和质朴的村民,也想起我们所养过的那 头猪。回首往事,我总想寻觅那种淡忘已久的感觉,再度品尝那种有着淡淡苦味却又令人难舍难忘的知青生活,但这些念头都已成为一种“奢望”了。| 欢迎光临 辽宁养老服务网 (http://bbs.lnylfw.com/) | Powered by Discuz! X2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