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潘少平
第966期
“过路郎中”之称,含有贬意。有句俗话,“过路郎中”医气卵泡,即:医不好,也医不坏。因是路过,看完病,收了钱,走人了事。显然,“过路郎中”名誉不好。而漆林镇张二毛偏偏有个“过路郎中”之称。
张二毛懂点医术,说起来,很为奇特。
张二毛小时候放牛,常在距漆林镇七华里的耸壁寺一带。寺里主持了尘和尚时已年届七旬,张二毛因常在此一带放牛,和了尘老和尚渐渐熟悉起来。耸壁寺一带水草茂盛,张二毛常把牛儿散放在这一带,任其自个儿吃草,自己却在寺中游乐。

张二毛有点小勤快,经常把了尘老和尚晒在竹匾中的中药、草药之类的翻翻拣拣。一日,了尘老和尚外出挖药未归,天突降暴雨,待了尘老和尚赶回寺中,所晒之药均已被张二毛收拾好了,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屋檐下,四周用稻草围得严严实实,一星半点都没有湿。了尘老和尚见此光景,说一声,天不下无根之水,佛不渡无缘之人,小施主,我们随缘吧。
从此,每遇张二毛来寺中,了尘老和尚总是拿出所晒之药,一一告知,此药叫什么名字,药味如何,药性怎样,能治什么病症。有时了尘老和尚拿出点枯枝残叶,加以说明,张二毛竟能在山上找到相应的药来。张二毛虽识字不多,却有小聪明,加之年少记忆力也强,虽不明了了尘老和尚的用意,却乐于识药辨味。一个有心讲法,一个随意听经,张二毛于此道也算入门了。
那时节、那年月,乡村中缺医少药。了尘老和尚精于岐黄,乡村中有人患病,常找了尘老和尚医治,了尘老和尚一律是免费的。其医术当然不在话下,所用之药皆是自己所采、所制。当然,待病愈后,患家十斤米一斤菜油送来,虽为酬资,却不明言,声称作为“香资”之用。这样送者欣然,受者坦然。

一日,一老者来到寺中,诉说自己脚手奇痒,且伴有小水泡,掐破水出,无色无味,又能自愈。自愈后又常复发,苦不堪言。老者一旁诉说,恰张二毛在一旁听闻,未及了尘老和尚说话,张二毛说道,老师傅(漆林镇不分男女老少,一律称了尘老和尚为老师傅),我记得你说过一个方子,专医这个毛病的。
了尘老和尚颇为吃惊,张二毛说,我记得是:生百部十钱、苦参十钱、千里光十钱、白癣皮五钱、地肤子三钱、蛇床子三钱、六味药煎水,泡手泡脚,半个月左右就好了。了尘老和尚说一句,孺子可教。又对老者说,就用这个方子。果然,老者照此方医治,半月后痊愈。
从此,了尘老和尚尽心教授,奈张二毛年少贪玩,学起来有一搭没一搭的。了尘老和尚却从不责怪,一切尽在“随缘”中。不过,张二毛能随口说个药方的事漆林镇人不晓得,那位老者不是漆林镇人,了尘老和尚不说与人知晓,张二毛也当做一件玩事而已。
那时节、那年月,乡村中人一般伤风感冒,是不会就医的,扛一扛也就过了。有些人伤风感冒严重些,常伴头痛、发热、鼻塞、咳嗽、流鼻水、打喷嚏、嗓子发干等症状。也合该张二毛要发迹了,一日,一人感冒,症候较重,张二毛叫其用葱白、生姜各五钱,食盐一钱,将其三味捣成糊状,用纱布包好,擦前胸、后背、脚心、手心、腘窝、肘窝,让其躺下休息,半个小时后竟汗出热退,各种症状随之消失。此人大奇,逢人便说,此事顿时传遍整个漆林镇。漆林镇人都戏说,这个张二毛还是个“过路郎中”呢,瞎猫碰上个死老鼠,医好个“气卵泡”。
此事传到耸壁寺,了尘老和尚竟说了一句,缘尽了。待张二毛再来寺中,了尘老和尚抚其头顶说,我要走了,这山上之药你用了吧。不过,你根基未深,以后切记,不知症不用药。张二毛有些茫然,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事,但却记住了“不知症不用药”这句话。这或是天资所然,或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心灵感应吧。了尘老和尚走时无人知晓。半个月后,寺中来了一位年青和尚。漆林镇人问了尘老和尚下落,年青和尚笑而不答。张二毛问之,年青和尚说,法师说了,寺中那些制药用的物件,你尽可搬去,一切量力而行。

自此,张二毛也装模作样地做起了“郎中”,漆林镇人有个头疼脑热的,也说,找“过路郎中”去。当然,张二毛仅能用一些偏方、单方医治一些乡村中的常见病。
那时节,乡村中儿童多发“黄水疮”,漆林镇人称为“脓疱疮”,此症好发于口鼻周围、颊部、手背及四肢。症榨较轻者,张二毛用黄瓜藤烧灰,用麻油(芝麻油)调之,搽患处。症状较重者,张二毛用槐树条烧炭存性,与雄黄末共研细粉,用麻油调之,搽患处。此法奇佳。把一些儿童的病医好了,家中大人感激非常,自然对张二毛高看一眼。张二毛袭了尘老和尚之风范,也一律不收费。不过,漆林镇人最重人情,逢年过节,自有礼物相谢。如家中有点好菜,非要拉张二毛去吃饭,其间当然要喝几杯,以至张二毛从不喝酒到喝一口,再喝一杯,到最后非半斤不过瘾,以致弄得每天晚上非喝一顿不可。
日久天长,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,加之张二毛已成年,已知学习之法的重要。医术再有大进,这是后话了。
书中自有颜如玉,这是劝人要好好读书学习,以后不怕找不到好老婆。郎中做好了,却也有颜如玉的。张二毛讨了桂花墩那个如花似玉的莲儿做老婆,就得益于此。

那时莲儿年方十八,正是豆蔻年华,却有一个难以启齿的“暗毛病”,就是月信期间,下腹部及腰部疼痛异常,难以忍受。无奈,告于母亲。母亲亦无奈,无奈之中,做娘的叫来张二毛,只说自己夜里困不着觉,又常头疼。张二毛来时,做娘的方叫来女儿,如此这般述说一遍。莲儿羞羞答答,满脸赤红,低着头,吱吱唔唔。
张二毛时已二十出头,已解风月,面对一个娇艳柔媚的大姑娘说出自己的难言之隐,又有一个做娘的在旁虎视眈眈,浑身不自在,竟不敢正视莲儿一眼。只得告知莲儿母亲,用咸盐二斤,醋一两,在锅中炒热,分装两包,轮流热敷于腹部。用丹参十钱,元胡七钱,共研细末,痛经期用黄酒冲服,每天两次,一次一杯。张二毛说完,忙叫莲儿母亲去炒盐,这药自己回家研好送来。整个时间,张二毛的头也未抬起一下,一反在别人家拿腔作调的模样,莲儿母亲不觉有点好笑。
就这样一剂方药下去,第二月,莲儿月信期竟毫无疼痛之感。莲儿母亲方觉得这个“过路郎中”不简单,不免在妇女群中聊起这事。妇女群中飞嘴短舌的,不免相互传说,张二毛能医姑娘家的“暗毛病”。以后莲儿的一些闺密竟私下相询,以至莲儿羞得几个月不敢出门。
俗话说,福至心灵。从此,张二毛每逢莲儿家有什么事,随叫随到,如在人家吃饭,竟放下饭碗就去,弄得这家人家莫名其妙。如莲儿父母有个头疼脑热的,张二毛殷勤备至,一天三趟,问寒嘘暖,弄得莲儿父母得意非凡,但张二毛决不和莲儿多说一句话,甚至连正眼也不瞧莲儿一眼。莲儿父母都说这个青年人是个正经人。
殊不知张二毛心怀鬼胎,这一切做经均为莲儿之故。(做经,皖南方言,意为“做作”之意)这都是张二毛交了桃花运,显得心灵意巧、心到神知。直至有一天张二毛因喝了酒,加之近来心情特好,不免有些过量,于人多处高谈阔论,恰值莲儿母女遇到。莲儿母亲自然热情招呼。莲儿斜视一眼说,又喝得酒鬼样。莲儿母亲责怪女儿说话无轻重,张二毛淡淡一笑,竟说以后不喝了。莲儿母亲闻言,有点丈二金刚摸不清头脑,回头望了望女儿,莲儿竟自去了。
待过了几日,镇上有人传言,张二毛戒了酒。此话传到莲儿母亲那儿,再想起女儿那句“又喝得酒鬼样”,才觉有了情况。不觉自笑道,这个青年人是个坏种,自己竟不知他何时和女儿搭上了,做得神鬼不知。自然免不了告诉自家老头子,老两口一合计,张二毛人品、家境也算不错,又说起为女儿医好了“暗毛病”,叹一口气说,也是缘法了。老两口也算得开明,且听之任之了。
此事发作后,漆林镇人多为张二毛说话。因为漆林镇人什么人都敢得罪,就是不敢得罪“郎中”,哪个人吃了五谷不生灾?哪个人沒有个头疼脑热?加之张二毛为人也不错,于是众口一辞,均极力促成此事。于是水到渠成,张二毛如意抱得美人归。
不过,婚后张二毛依然喝酒,旧习复萌。莲儿也奈何不得,私下处,莲儿骂张二毛是个骗子,张二毛说,那个叫你得了个“暗毛病”,我不去你家,不就没事了。莲儿羞得拿起扫帚来打,张二毛高声喊救命。莲儿怕人听见,只得含羞作罢,小两口自是一番恩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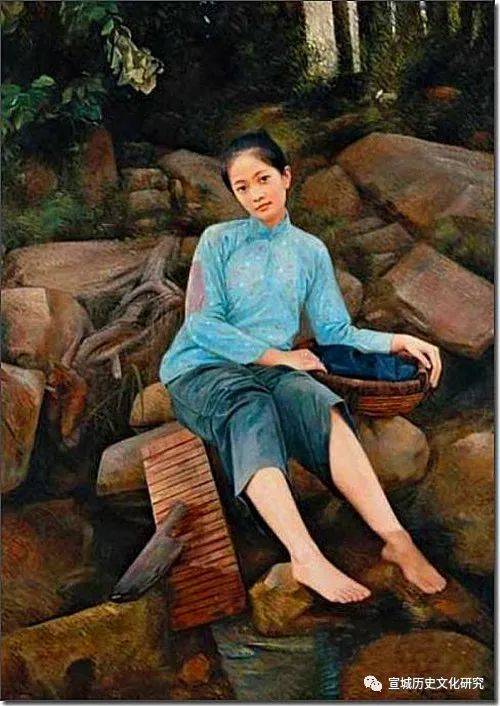
莲儿本就天生丽质,婚后,张二毛更是每年均采来些许桃花,加冰片,用蜜糖搅拌成汁,供其擦拭。常年使用,使得莲儿是肌色莹润,脸似桃花。惹得莲儿的一些闺中密友称羡不已,免不了怪自己老公没本事。此话传到莲儿耳中,莲儿不免一番得意。女人家天生善妒,如有一些女人来找张二毛看病的,又有点姿色的,莲儿免不了私下对张二毛说些三角钉(三角钉,皖南方言,意为“话中有话”)的话,敲敲打打。不过,张二毛有柳下惠之德,坐怀不乱。
张二毛婚后,再替人看病,开始收点钱了,成家立业,养家糊口,镇人都能理解。但张二毛收费,总是看人家境而为,家穷者收费偏低一点,落一个好口碑;家富一点的收费高些,富家亦能接受,吃药是不问价的,只要病好快一点就行了。所以,张二毛收入颇丰,家境殷实。双亲健在,仍能劳作,小两口恩爱,日子过得风调雨顺。
(作者系泾县缫丝厂退休人员,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)
制作:童达清
潘少平
第967期
时至公元一九四一年“皖南shibian”事发,guomindang的一个营进驻漆林镇,搜捕xinsijun伤员,并清剿xsj游击队。对于xsj,漆林镇人都同情拥护,痛恨gmd军队时常扰民,强买强卖。那时xsj游击队缺医少药,处境十分艰难。张二毛常暗中送医送药,以钱物接济。
那时进购药品十分困难,须得这个smd军队营部的特别凭照。精明的张二毛却有个好法子,借自己行医之便接近营部的这个军医,以请教为名,向他学习西医。其间当然免不了要吃点饭,喝点酒。这个军医嗜酒如命,但酒量不及张二毛。张二毛酒量从小练就,非一般人能及。两人喝酒,十次这个军医要醉九次半。军医醉酒后,如有士兵来因病就医,张二毛自告奋勇,以替诊治,待患病士兵得到诊治临走时,张二毛又塞上一包香烟,说自己不该和军医长官喝酒,险些误了事。张二毛医术比这个军医高超多了,当然手到病除。事后,患病士兵高兴,军医醉酒后又不误事,大家皆大欢喜。久之,二人竟称兄道弟起来。

又一日,两人在一次喝酒,张二毛借机说道,老兄呵,药品难买,最近用药又多,自己要关门息张了。军医说道,兄弟你早说呀,我也知道你为我们当兵的用了不少药,昨日我还和我们营长说起你,说你拥护政府,给当兵的医病不要钱,够朋友呢。啰,我补你点药。明日去我处拿。这个军医因常被请吃,正好借机意思一下。
张二毛精明之极,趁机挨近军医,摸出两块大洋,塞进军医荷包里。军医假作推托,张二毛假装变色说,看不起兄弟。军医忙举杯说,兄弟,喝酒喝酒。张二毛又借机说,你晓得的,我常去外地看病,但总不能天天去呀,每一次去外地看病,看一处,总得给人家留下十天、半月的药,我用药量大呵。军医又举杯说,兄弟,好说,好说。开个单子,我给你买来。喝酒喝酒。
酒足饭饱,军医跌跌撞撞地站起来,要去付帐。张二毛一把拉住说,兄弟,你放心,不会托你买药,你为难,这个帐我付了。军医卷着舌根说,看不起兄弟,你明日开单子来,老哥不给你办到,我是biao……biaozi养的。
第二日,张二毛开来单子,果然军医包了一大包药,并说,这是补你的药,我们营长知道的。军医拍了拍药包说,兄弟,拿好呵。你这个单子,十天半月内准给办到。张二毛提了药包出门,门口站岗的士兵张二毛曾给看过病的,张二毛指着药包,大模大样地对这个士兵说,这是你们军医长官补给我的药,你们营长批过了的。说完,又塞上一包香烟。士兵接过,讨好地说,才补了这点药呵,我们营长也太小气了。
张二毛回家,打开药包一看,都是紧俏药品,市面上买不到的。翻到最后,吓了一跳,竟有二支盘尼西林(青霉素)。这市价可是二担稻谷一支呵。当然,这包药晚间就送去xsj游击队了。事后,新四军游击队里传来话,这包药可是救命之药呵。
半月后,军医果然买回药来,并明目张胆地派人通知张二毛来拿。张二毛虽有疑惑,但又不得不去。到时,军医拿着个单子,叫张二毛同去营长处查验一下,并把个单子晃了一晃说,兄弟,去营长处查验一下,保你无事。
到了营部,军医报告说,这次购药,连带着给张二毛进了一点药,说着把单子递给张二毛,快叫营长派人查验呵。张二毛接过单子一瞄,就心知肚明了。这单子并不是自已开的那张,单子上的药大都市场上可以买到的。张二毛也算得半个江湖人了,见机忙说,怎么有些药没有买到。军医说,有些禁药,不可乱买的。营长看看张二毛,觉得这人也算厚道,也晓得他经常给士兵看病的事,说道,查验什么,按规定能办的办了就是了。

恰在此时,营长太太走了进来,看一眼张二毛说,你就是跟耸壁寺老和尚学医的那个“过路郎中”吧,我最近有点咳嗽,你给看看,我不喜西医,动不动就打针。我相信中医,我不怕喝那碗苦水的。
张二毛知道这个营长太太识文断字,原是个女学生呢,长相也不错的。忙机智地接道,我看不过受凉之故,注意饮食,再好好调养一下,谅无大碍。这也巧了,我手头恰有一支老山参,值不了几个钱,我回家取来,太太不嫌的话,泡点水喝喝,调养调养,大概有点用处。营长一听忙说,那好呀,钱是要给的。张二毛说,等吃了有用处,我再来讨钱也不迟呀。我回家取去。军医说,你把买来的药带回去。张二毛说,不急,反正我马上回来。
说完,张二毛忙要赶回家去。军医随之出了营部,于僻静处悄声说道,兄弟真会来事呢。张二毛回道,上次药包内的两支东西我外出看病时用了,真灵呢,也卖了个好价钱。说着掏出两块大洋塞去。军医一见,说太多了吧,一人一半。张二毛说,上次那包药我收了呢,老兄就是向我讨钱我也不给的。啰,这次是替我买药的一点辛苦钱、跑腿费。虽然亲兄弟、明算帐,老弟可是赚你的多些。军医哈哈一笑说,真服了老弟了,会说话,会做事,更会做人。
因了张二毛与营长太太的这一次交往,张二毛买药方便多了。营长太太贪点便宜,张二毛投其所好。营长睁一眼闭一眼,只图太太高兴。军医图个大洋叮当响。其每次所购之药大部分都交给了新四军游击队。

其间有一次给xsj游击队购药,张二毛玩得太漂亮了,其机谋简直是诸葛再世。因这次xsj游击队接受了上级领导的一次购药任务,所需药品紧俏,属禁售之例。药品需量也大,一次性购买,太危险了,万万不可的,分批次购买,周期太长了。因为急需,时不待人,岂能让伤病员们等药呵。张二毛也觉为难,就算自己外出行医用药量大,也大不到如此程度呵。
张二毛找了军医,开了单子,说这次买药有点多,不敢瞒老哥,有几个同行的也想托我买点。单子上注明的那些药,价格我翻了三番,如能买到,老哥七成分帐,我只得三成赚头。营长那儿我去打点,不知老哥怎样,如难办,也就算了。军医见利眼开,咬咬牙说,量是有点多,不过,我来办办看。
又是半个月后,军医果然买回药来。张二毛说,这次药量大,我叫两个人晚上来,我俩先去喝酒,待天黑后再运回家,避点耳目、遮点嫌疑。军医喜滋滋,说张二毛如能是他们的营长,带兵打仗就能百战百胜,点子多,主意高呢。二人喝酒,张二毛极为高兴,说认识这个老哥,简直等于遇到一个财神菩萨,别人办不到的事,你老哥轻而易举地就办到了。军医得到夸奖,又因购得药回,心情极好,又加贪杯,放量喝了起来,杯杯见底。
天快黑时,运药的人来了,几次催运。张二毛说,等一下,让我和老哥尽兴一下。运药的人不高兴了,说我们也要赶回去吃饭呢,肚子有点饿了。张二毛说,急什么,找老板去弄个菜,打点酒吃去,记我帐上。运药的人高兴了,你们慢慢吃,我们等,等到天亮都行。这顿酒也不知喝到什么时候,军医也不知怎么回的家,待第二天醒时,才知药已运走了。军医感觉很好,只等那七分红利入帐了。军医很放心,自己无本生利,做的是干股生意。张二毛向来一是一、二是二,自己赚了不少了。
等到下午时分,张二毛托人带来口信,叫军医去他家一下,军医欢天喜地,以为去他家分利钱了。待到了张二毛家一看,吓了一跳,张二毛躺在床上,额头破了一块,在床上哼哧、哼唧的。说道,老兄呵,你这次替我购药,做得太利索了。昨日一高兴,多喝了一杯,天杀的那两个挑药的因为喝的是不要钱的酒,也喝的黄猫不认得黑猫,昨晚天又黑,回家时不小心,连人带担子从桥上跌下了河,我稀里糊涂来捞药,竟跟着跌下去,也算祖宗积德,留了条小命。这批药算完了,那两个挑药的杀坯睡在家中在装死呢,你去看看。
军医大惊,忙说,老弟呀,破财免灾,你身体怎样呵,无事就好。张二毛从枕边摸出十块大洋,递给军医说,老兄呵,兄第这次对不起你了,说话不算数了。军医做的是无本钱的生意,任你这批药霉了烂了,与他无涉。见此光景,也不免假意推辞一番,奈张二毛执意不允,自然就坡下驴子,收下十块大洋。
过了几日,张二毛来找军医,头上的伤已结了痂,光鲜明亮的。军医又陪张二毛来到营部,拿出一支上好的参,送给营长太太。营长问其头上的伤,张二毛如此这般、绘声绘色地说起酒后跌下桥底的事,军医在一旁又添油加醋地加以补充,说道,张二毛这次亏惨了,还好,保了条小命。张二毛说,营长呵,实对你说了吧,几个同行的托我带买点药,我也收了他们的钱了,本想以翻三番的价再卖给他们,这次连本带利,鸡飞蛋打了。我想家中还有十亩田,全抵押了,凑点钱,再购点药,我只要一番的利,还有二番的利算你们营部的开支,我只要把我几个同行的钱补齐就行了,我亏的就算了,不然,在同行的面前我混不下去呵。军医在旁听得张二毛如此说道,心里有点不自在,但一想这次张二毛亏大了,也只有如此了。如再购药,没有营部的批文是万万不可的了。

营长太太一旁听闻,忙说,不要紧的呵。看看我们家营长能不能帮点忙,我也有几个私房钱,借给你,我们说好了,到时还我本钱就行。营长太太这番话,鬼才信呢,她是借机做买卖了。张二毛一听,说道,好说,药买回来后,我保证三日之内还钱。营长说,此事天知地知、人知鬼知,说完横了军医一眼。军医是个拍马溜须、掼于扯顺风旗的人,忙说,张二毛你开个单子来。
张二毛回家后,托人如实向游击队领导说明了事由。游击队领导认为可行。并带来了钱款,张二毛一不做、二不休,竟将十亩田如实抵押了。凑了钱款,开了药单子,交给了军医。并要军医悄悄地告诉营长太太,她借的钱另行买药,交给自己就行。军医当然如实相告,营长太太喜笑颜开。
又是半个月,军医带来口信,说药买回来了。张二毛来到营部一看,连自己也吓一跳,药量如此巨大,药的品种如此全齐,有些违禁药品是市场上没有的。营长一脸严肃说,张二毛呵,我可是尽了力了,下不为例了。如上峰查下来,我也不好办呢。营长太太一旁娇滴滴说,我只要本钱就行了,你不要为难呵。张二毛说,太太你放心,这次运药,是不喝酒的了,要喝,到家才喝。不过,请军医一同随我运药回去,三日后我同军医一同来还你的钱。营长太太笑成一朵花,说这样最好,这样最好。营长也说,三日在我家喝酒,我太太也会烧几个菜呢。营长太太一旁说,一定来,一定来呵。张二毛说,一定来!一定来!只是不要太破费了,我家里还有二瓶好酒,存了五年了,到时带来!
于是,张二毛和军医一道把药运回家中。营长太太静候佳音。第二日佳音果至,军医如同死了娘老子一样,拿着一封信浑身抖成一个筛糠的样子,交给营长。营长情知不妙,打开信看时,信上写道:药品如数收到,实为我游击队急需。此事望你部酌情处理,但此事尚以不扩散为好。另:张二毛已归队,此事也以不扩散为好。营长大怒,一巴掌挥向军医,说你昨晚干什么去了。军医说,昨晚喝醉了。这时,营长太太一旁长嚎,我还有三百大洋的本钱呢。营长又是一巴掌挥过去,说,你作死呀,嚎什么丧,怕人家不知道呀。此事,营长吃了个哑巴亏,自然不敢声张。如声张开来,自已太太还有三百大洋充了“敌资”呢!

但此事在漆林镇竟不胫而走,以前有人人为张二毛和gmd军队勾勾搭搭,极为不齿。此事一出,才知张二毛深藏不露,是个很有本事的人。最后又笑说,张二毛是个真正的“过路郎中”呢,捞了一笔,就走了。以后又有人传话说,张二毛一次在游击队里喝酒吹牛,说自己这辈子喝酒没醉过,那些个gmd的军队想赚我的钱,也不掂掂自已几斤几两,先花点小钱,以后连本带利地捞几个番番过来。不过,自己也花了血本,一砖头把自己的额头敲破了皮,有点不值得。漆林镇人却说,这个牛皮也只能由他这个“过路郎中”吹呢。
二十年后,张二毛由正营级职务退休回漆林镇。镇人以首长称之,张二毛不允。说自已还是个“郎中”嘛。张二毛从旧习,为镇人免费医治病痛,一如从前。暇时和镇人喝酒吹牛。
时光飞逝,转眼又至公元一九liuliu年,“wenhua大geming”事发。张二毛审时度势,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带头“zaofan”。镇医院成为“漆林镇卫生战线革命zaofan总指挥部”, 张二毛当仁不让地做了总指挥。而那个耸壁寺却成了“漆林镇东方红卫生室”。张二毛说,我们要响应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”的伟大号召,我们漆林镇卫生战线要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田间去”。漆林镇四周有近万亩田地,是农民阶级兄弟战斗的广阔天地,我们要去服务。张二毛带人把耸壁寺所有的菩萨、法器之类来了个集体封存,并说不准损坏,因为这是进行阶级douzheng教育的活教材。
也有人对张二毛此举不理解,张二毛托人传话过去说,别和我们这些“郎中”过不去,吃五谷,生六灾,头虽不痛,脑要发热。与人方便,自己方便。听得此话的人果然有些忌惮,心虽不甘,也只能默认此事了。因为遇上“生六灾”、脑发热的事,还是要靠这些人,毕竟是一个镇上的人,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

正因为张二毛的这个举止,耸壁寺竟免了打砸之灾,整个寺院完好地保护下来。据说,一次夜静更深,有人见张二毛沿着耸壁寺转圈圈,并听得张二毛朗朗自语:师傅呵,我也尽力了。我在一天,力保这寺庙一天,你老在天之灵,也要助助我呵……时过境迁,世人对这座江南名刹的完整、完好啧啧称羨,已是后话了。
张二毛享年八十八岁,已届米寿。临终前上级派员看望,张二毛懂得其中奥妙,说,我个人没有任何要求,死后火化,要葬在耸壁寺旁,自己生前没有为师傅做过一件事,尽过一次孝,也不知师傅仙逝何处,圆寂何方,死后埋在耸壁寺旁,弄个土堆堆,也算是师徒一场的情份吧。此事上级部门有些为难,但漆林镇人却不管这些条条框框的,果然在耸壁寺旁弄个土堆堆,立一石牌牌,上书“过路郎中张二毛之墓”。
(作者系泾县缫丝厂退休人员,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)
制作:童达清 。
| 欢迎光临 辽宁养老服务网 (http://bbs.lnylfw.com/) | Powered by Discuz! X2 |